

中芯国际近日发布了超预期的二季度业绩,这折射出半导体产业链业绩复苏趋势愈发明显。与此同时,投资机构近期密集调研该板块,探寻该产业复苏的可持续性。


Choice数据显示,7月以来,已有55家A股半导体上市公司(统计口径:申万行业分类)获得机构调研。其中,有公司接待了12个批次的机构,有公司接待机构数量合计达到402家。从产业链角度看,机构对半导体设计公司调研热情最高,对并购重组、下半年产业趋势等问题最为关注。
对此,有半导体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半导体产业逐季向好,复苏态势超预期;随着下半年AI手机等销售旺季到来,以及智能汽车销售增长,预计半导体全产业链复苏还将加快。(上海证券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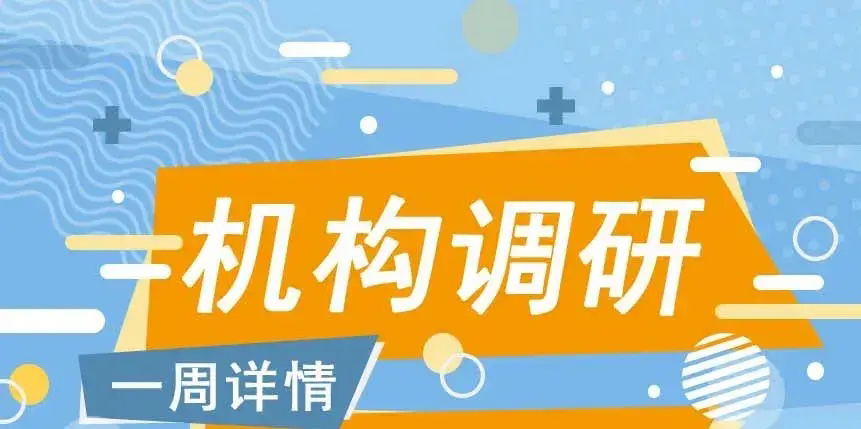

半导体芯片概念股编者按:全球芯片产业景气正在持续升温,而国内半导体产业则有望迎来“黄金十年”。 国际半导体设备材料产业协会(SEMI)近日公布,6月北美半导体设备订单出货比由5月的1.00升至1.09,触及2013年11月以来高点。 据了解,该指标是观察半导体景气重要指标,大于1代表厂商接单良好,对未来保持乐观看法。 华天科技:成本技术管理优势兼备 未来持续快速增长可期华天科技 研究机构:申银万国证券 分析师:张騄 撰写日期:2014-07-14三地布局完成,成本技术优势兼备。 公司已完成昆山、西安、天水三地布局,高中低端生产线分工明确,成本技术优势兼备。 昆山华天已全面布局WLCSP、Bumping、TSV 等先进封装技术。 西安华天和天水华天进行中低端封装,成本优势明显。 管理层直接控股,股权结构优势显著。 公司12 名董监高管理层中,有9 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公司母公司42.92%的股份。 这一股权结构使得公司大股东、管理层和中小股东利益保持高度一致,股权结构优势显著。 Bumping+FC 业务年底启动,未来高增长可期。 预计昆山华天将在今年四季度开始进行12 寸Bumping 的大规模量产,月产能将达5000 片。 随着Bumping市场规模的快速增长,公司有望快速扩大产能,并且还将带动西安华天FC 业务的快速增长,未来高增长可期。 MEMS 封装技术优势明显,静待大规模量产时机。 MEMS 进入快速发展第三波,未来几年将成为WLCSP 封装技术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公司将进行8 寸产品的生产,较目前主流的6 寸MEMS 产品具有更好的一致性,主要产品包括加速度计和指纹识别两个领域,将静待大规模量产时机。 首次覆盖,给予增持评级:我们预计公司14-16 年EPS 为0.40 元,0.52 元,0.62 元,对应14-16 年的PE 为28.2X,21.8X,18.2X,我们认为公司先进封装业务、中端封装业务、低端封装业务合理估值水平分别是15 年40 倍、30倍、20 倍,对应目标价为13.32 元,首次覆盖给予增持评级。 核心假定的风险:1)国家集成电路扶持政策落实低于预期;2)Bumping 大规模量产时间推迟;3)基于WLCSP 的CIS 产品需求出现下滑。 晶方科技:业绩符合预期 长期受益进口替代晶方科技 研究机构:山西证券 分析师:张旭 撰写日期:2014-04-01事件追踪:公司公布2013年年报。 公司2013年营收4.5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53%;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5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47%;基本每股收益为0.8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6%。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7.5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73%。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不送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事件分析:受益行业复苏,公司营收稳定。 2013年,受益于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半导体市场增速出现周期性回升。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产品持续增长的带动下销售同比增长16.2%。 在整体产业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出现了差异分化的增长态势,其中封测业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增长率为6.1%。 在此背景下,2013年公司持续专注于传感器领域的封装业务,把握CMOS、MEMES、智能卡、生物身份识别等芯片领域发展的有利时机,全年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 公司是大陆首家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厂商。 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技术的特点是在晶圆制造工序完成后直接对晶圆进行封装,再进行晶圆切割,封装后的芯片与原始裸芯片尺寸基本一致,符合消费电子短、小、轻、薄的发展的需求和趋势。 目前,该技术只有少数公司掌握,公司作为中国大陆首家、全球第二大能大规模提供影像传感芯片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量产服务的专业封测公司,具有技术先发优势与规模优势。 公司将长期受益进口替代,发展空间巨大。 目前外资企业在我国芯片制造和封装测试销售收入中所占比重已超过80%,国内集电企业面临严重考验。 同时,随着国内消费类电子需求的持续增长,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类电子市场。 持续增长的消费电子需求,也是我国集成电路企业面临的良好发展机遇,公司长期受益进口替代。 盈利预测与投资建议:盈利预测及投资建议。 公司是大陆首家晶圆级芯片封装厂商,技术处于行业上游。 随着国内市场的全球地位日益提升及国内产业政策的持续推动,我国集成电路市场将成为全球最有活力和发展前景的市场。 公司未来发展空间较大,我们看好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考虑到近期半导体扶持政策的出台预期,首次给予公司“增持”投资评级。 投资风险:行业波动风险;汇率波动风险长电科技:卡位先进封装 业绩拐点确立长电科技 研究机构:申银万国证券 分析师:张騄 撰写日期:2014-07-07卡位先进封装技术,成长路径明确。 公司现在是国内封测行业规模最大,全球第六大的龙头企业。 公司凭借规模优势在先进封装技术研发支出上远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提前卡位先进封装技术,实现先进封装技术的全布局,勾画出明确清晰的中长期成长路径。 Bumping+FC业务确定性高成长。 当芯片制程进步到40/45nm以下时, Bumping+FC封装方法成为必然选择。 今年是28nm规模化量产大年,Bumping市场规模将快速增长。 公司在这一领域已经有多年技术积累并实现大规模量产,受益于行业趋势将获得确定性高成长。 年初牵手中芯国际更是锦上添花,有望切入国际IC设计大厂高端产品。 TSV和MIS技术领先,未来成长空间巨大。 公司在TSV技术和MIS材料两个领域技术领先,未来这两个领域都将坐拥近百亿美元的市场空间,并且高速渗透期拐点即将到来,有望成为行业规模爆发增长的最大受益者。 2Q业绩拐点确立。 公司7月2日公布业绩预增公告,2Q单季实现净利润5000万元左右。 这主要受益于低端生产线搬迁阵痛结束,人力成本优势显现;先进封装技术前期大额研发投入之后,随着量产规模提升开始进入业绩释放期;并且快速增长的先进封装业务对公司整体业绩推动作用加大,2Q业绩拐点确立。 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我们预计公司14-16年EPS为0.24元,0.42元,0.67元,对应14-16年的PE为42.5X,24.1X,14.9X,我们认为公司先进封装业务、中端封装业务、低端封装业务合理估值水平分别是15年40倍、30倍、20倍,对应目标价为12.67元,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核心假定的风险:1)盈利恢复无法持续;2)国家集成电路扶持政策落实低于预期;3)中芯国际先进制程量产出现问题。 同方国芯:核心芯片国产化是趋势 只是需要耐心同方国芯 研究机构:长城证券 分析师:金炜 撰写日期:2014-04-28投资建议公司作为国内智能卡芯片厂商第一梯队成员,手中既有类似二代身份证芯片的现金流业务,也有即将爆发的金融IC卡及移动支付产品储备,在核心芯片国产化的趋势下,公司将稳步受益。 另外国微电子作为军品特种元器件行业龙头企业也有望稳步受益于军队信息化建设。 公司后续仍会考虑进行一系列的收购快速进入其他集成电路产业。 我们预测公司2014-2016年EPS分别为1.18元、1.59元及2.08元,对应目前股价PE分别为36x、27x及21x,维持“推荐”评级。 投资要点公司一季度营收净利润同比均双位数增长: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6.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21.0%,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87.9%。 公司传统业务保持稳定增长,金融支付类产品和特种集成电路新产品正逐步进入市场,开始贡献收益。 公司一季度毛利率提升:公司一季度整体毛利率为32.1%,相比去年同期的30.4%有所提升。 预计主要是4GSIM卡芯片以及国微电子业务提升。 公司一季度费用率控制较好:公司一季度费用占比为15.1%,相比去年同期的18.5%有较大幅度下降。 公司应收账款占比上升:公司一季度应收账款为4.70亿元,占收入比为255.3%,相比去年同期的244.5%略有所上升。 存货相比去年同期无大变化。 公司经营性现金流比去年同期好:公司一季度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4380万,比去年同期向好。 n2014年SIM-SWP卡芯片以及金融IC卡芯片恐尚不能为公司带来较大收益,但我们对公司2014年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30%仍较为有信心,原因如下:二代身份证芯片将作为公司现金流业务长期存在:公司作为公安部一所指定的四家二代身份证芯片生产厂商之一(其余三家是中电华大、华虹设计和大唐微电子),从2003年以来便为公安部提供二代身份证芯片。 由于居民信息的保密原因,十年间,公安部没有再通过其他芯片厂商的认证。 我们预计二代身份证芯片业务将长期作为公司的现金流业务存在,为公司整体业绩提供保障。 公司营业利润中34%左右均来源于身份证芯片业务,只要该项业务公安部不引入新的竞争者,公司业绩将有较为稳固的基础。 另外考虑到2005-2006年是身份证发证高峰,2015-2016年恐有一波换证高峰到来,我们预计2014-2016年公司身份证芯片业务将呈现稳中有升的局面,为公司总体业绩增长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公司SIM卡业务将持续增长并提升毛利率:公司去年SIM卡出货量约7亿张,同比2012年增长56%。 在单价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公司毛利率从6%左右提升到了12%-13%。 全球一年发行50亿张SIM卡,公司目前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约14%。 我们预计在规模化效应下,公司的SIM卡发卡量将进一步上升,另外由于大存储的4GSIM卡采购占比上升,公司SIM卡毛利率仍有望进一步提升。 我们预计公司今年有望发行10亿张SIM卡,毛利率将接近15%,预计为公司提供4000元左右的营业利润,占到公司总体营业利润的10%以上。 受益于军队信息化建设提速,国微电子将维持25%-35%左右业绩增速:同方国芯旗下另一家子公司国微电子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设计、开发与销售,公司具有全部特种集成电路行业所需资质。 公司是国内特种元器件行业龙头企业,是国内特种元器件行业门类最多、品种最全的企业。 截至目前公司完成了近200项产品,科研投入总经费9亿余元,其中“核高基”重大专项支持经费3亿多元。 和同行比,公司产品种类最全,品种最多,目前可销售产品达到100多种。 国微电子在研项目转化产品能力较强,在研项目超过50项,年均新增产品近30项。 我国军工用的集成电路市场总额为60亿,国内的公司仅占了其中6个亿,国有军工企业有较大发展空间。 我们看好国微电子在军队信息化建设浪潮中的发展,也看好公司军转民的尝试。 公司有望2015年受益于金融IC卡芯片国产化:目前我国银行卡业正在经历EMV迁移,各家银行的磁条卡正在初步替换为芯片卡,2013年全年新增芯片卡约为全年新增银行卡的47%。 我们预计2014年全年将新增4-5亿张芯片卡,主要来源于股份制银行的发力,芯片卡渗透率将进一步上升。 目前各家卡商基本均采用NXP的芯片,随着华虹设计通过了CC的Eal4+认证,国内芯片厂商与外资芯片厂商的技术差距正在进一步缩小。 目前发改委正在组织包括同方国芯在内的几家芯片公司进行局部区域的规模发卡测试,一旦安全性得以验证,在国家信用的背书下,国内银行将逐步采用国产IC卡芯片替换进口IC卡芯片。 我们预计2014年将是国产芯片厂商崭露头角的一年,经过一年实网测试后,国内芯片厂商有望在2015年与国外厂商正面竞争,届时成本将是考量国内芯片厂商是否能获取市场的重要因素。 核心芯片国产化是大趋势,国产芯片企业正在缩小和国外企业的差距,这个时候需要的是耐心。 投资建议:公司作为国内智能卡芯片厂商第一梯队成员,手中既有类似二代身份证芯片的现金流业务,也有即将爆发的金融IC卡及移动支付产品储备,在核心芯片国产化的趋势下,公司将稳步受益。 另外国微电子作为军品特种元器件行业龙头企业也有望稳步受益于军队信息化建设。 公司后续仍会考虑进行一系列的收购快速进入其他集成电路产业。 我们预测公司2014-2016年EPS分别为1.18元、1.59元及2.08元,对应目前股价PE分别为36x、27x及21x,维持“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2014年SIM卡芯片价格战,公司健康卡销售不及预期,国微电子盈利不及预期。 七星电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设备制造商,以集成电路制造工艺技术为核心,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设备、混合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为主营业务。 公司拥有优秀的技术研发团队,具备一流的生产环境,加工手段和检测仪器,是中国最大的电子装备生产基地和高端的电子元器件制造基地。 是“六五”至“十五”期间承担国家电子专用设备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骨干企业,国内唯一一家具有8英寸立式扩散炉和清洗设备生产能力的公司。 公司生产的混合集成电路等军工配套产品在“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嫦娥一号”、长征系列火箭的航天任务和多项国家重点工程中得到应用。 上海新阳公司是以技术为主导,立足于自主创新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半导体行业所需电子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同时开发配套的专用设备,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化学材料、配套设备、应用工艺、现场服务一体化的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主导产品包括引线脚表面处理电子化学品和晶圆镀铜、清洗电子化学品,可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制造、封装领域。 公司产品主要基于电子清洗和电子电镀核心技术。 公司设有专门的研发机构,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研发水平高超的专业研发队伍,取得了3项国家发明专利、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和多项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公司被中国企业创新成果案例审定委员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认定为“最具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先后被评为上海市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上海市科技创新企业、上海市专利工作培育企业、上海市重合同守信用AAA级企业。 中颖电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从事IC产品的设计和销售,并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及技术服务。 公司所设计和销售的IC产品以MCU为主,产品主要应用于小家电及电脑数码产品的控制。 公司是首批被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及上海市信息化办公室认定的IC设计企业,并连续11年被认定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在国内已取得10项发明专利和4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在我国台湾地区获得发明专利5项,已登记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84项,已登记的软件著作权7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