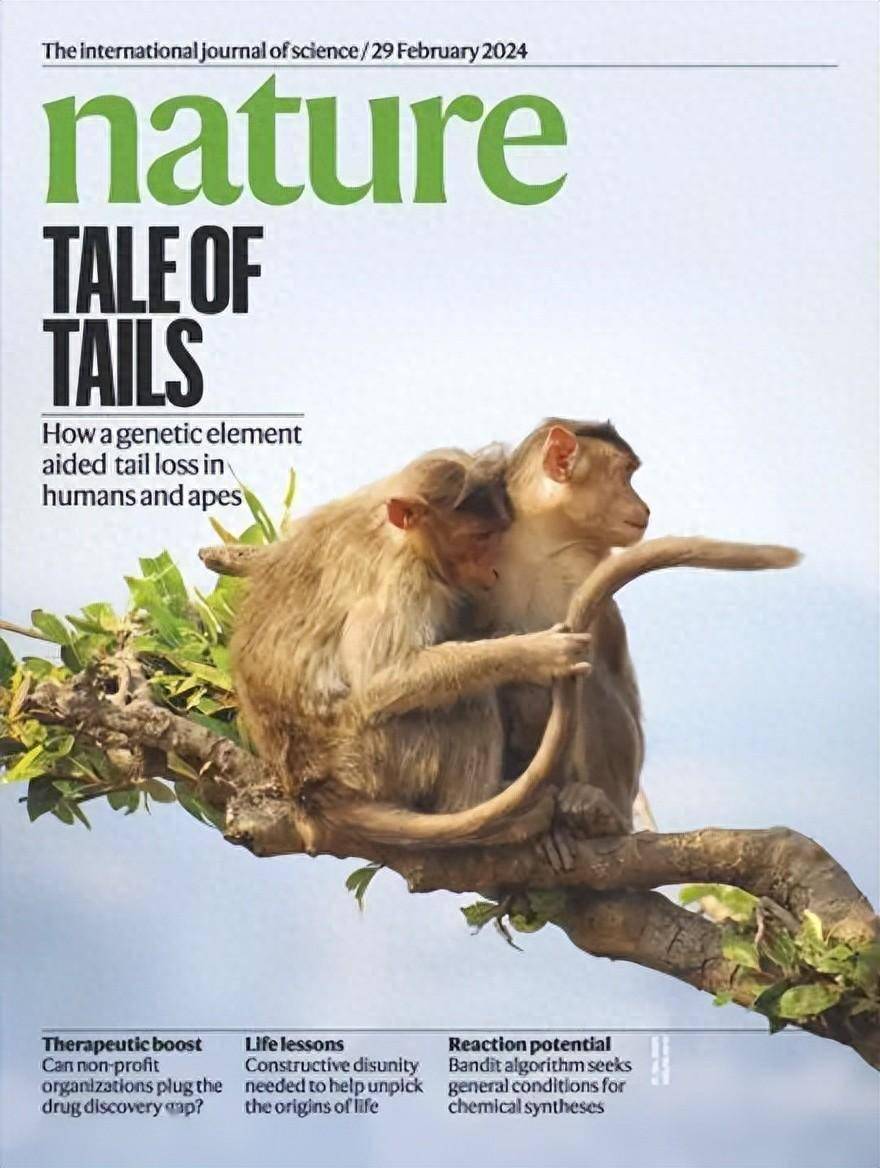作 者 |南风窗 记者
编辑 |

5月,南京林业大学青年教师宋凯自杀离世引起关注。在此之前,他未通过学校首个聘期的考核,亲属称其患有抑郁症。这一事件也将大学青年教师的困境又一次带出水面。
曾经,这是一个不被重视的话题。大学老师有编制,一年有寒暑两个长假、体面又有地位, 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们的苦与累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即便今天,这种印象仍然存在。
其实形势早已变化。合同制、“非升即走”的“预聘-长聘制”,正打破大学青年教师的“铁饭碗”;熬夜打磨社科基金项目申请书和论文的春节,其实并不好过;一位入职北京某211大学一年半的博士后讲师此前告诉南风窗,到账的税后月薪只有7千多;舆论场上,大学教师的整体形象和地位也在滑落。
如何改善处境的话题,贯穿在高校青年教师的社群讨论里。 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权威期刊学术论文篇数、申请基金项目的级别;评上“副教授”职称,是待实现的目标,也正成为“学术圈”新的准入门槛。
过程中,高校教师评价“唯论文”“唯项目”“唯职称”“唯奖项”“唯帽子”的痛点问题,由此显现。
挣扎求存、竞争上升中,我们发现,指标管理与量化评价之下,教育评价的标尺趋于单一,指挥棒如此强而有力,功利的应许充满诱惑,这不仅侵蚀着高校青年教师的自主性,也让他们对坚持教学、学术、科研的本心,有了动摇和分歧,进而成为大学教育向新与活力的一重阴影。
大学校园里,“水课”让人又爱又恨
学生嫌弃它,因为内容低阶且陈旧,上过和没上过一个样,却又为了轻松拿高分提高绩点,在评奖、保研、留学中占得先机,对它青睐有加。
教学质量是教师考评的基础内容,去“水课”而捧“金课”本是应有之义,但现实中,考评却难以淘汰它。
操太圣是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在研究教育政策和教师教育问题时,就曾探究这一现象的成因。他告诉南风窗,现行针对高校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价中,学生是评价主体之一,但学生评教却几乎失效。
“如果满分5分,大部分老师往往都是4.5分以上,没有区分度,最后流于形式。”操太圣告诉南风窗,与此同时, 以“分数”为核心,教师和学生在结果上形成了微妙的等价交换关系 ,“学生给老师打的分高,老师给学生打的分也高,这个水课就可以常年开下去”,反倒是不轻易给高分的老师,哪怕课讲得好,一些学生也宁愿去旁听而不是选修。
在此之上,即便一些学院设置了督学督导,由行政部门、学院中层、教师之间旁听以作多元评价,但人员和精力不足,也碍于熟人社会之中的情面,效果不佳。
“其实教学这件事很难评价。”操太圣说,一位老师的课上得好不好,对学生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短期不见效,也说不清关联,一个学生成才也很难说是某一位老师的功劳。
最后学校往往采用最基本的要求,“看你一学期给学生上了多少节课,有没有达到课时量要求,有没有师德师风问题,有没有教学事故,大家也就大差不差了”。相比之下,老师在学术科研上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区分度更明显。
另一边,以学术论文、科研基金项目为核心的学术科研成果是考核的硬性指标,也是教师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它不止针对教师,更首先适用于高校。
事实上,不同水平的学校也都处在追赶状态当中,“985”“211”类学校要追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本科院校也在申请成为硕士点、博士点,而学术论文、科研基金项目作为显著、易测量的成果,成为高校竞相追逐的赛道,长期以来,推就了“轻教学重科研”的倾向,也反映出了资源在往哪里倾斜。
考核之下,轻教学重科研
对学术和科研的倚重,通过高校的管理考核,向教师传导压力。
“学校给各个学院下达科研的指标,明确每年要完成的科研任务,学院再把指标分解到老师身上,学术工作就被纳入到行政管理当中,再定期进行考核评价,看是否达到目标,就有相应的奖惩措施跟进。”操太圣说。
这和企业绩效管理并无不同,但“胡萝卜+大棒”的方式,通过多个侧面影响老师的教学积极性和自主性。
2019年,余薇入职一所“985”高校,“预聘-长聘”的6年考核期里,她在3年的中期考核就经历了“非升即走”。
余薇在3年的中期考核就经历了“非升即走” / 《黑狗》剧照
她在社交平台记叙了经过和落选时的错愕,“学校把我们这种已经工作3年的青椒和新来应聘的人放在一起竞争,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只关注科研产出,而我还傻乎乎地分为‘科研、教学、社会活动’三方面进行陈述……事后回想,五味杂陈。”
张墨是广东一所二本院校的青年教师,在她看来,这所学校以教学为主,但也提出了“ESI工程科学学科全球排名前1%”的目标,且设有多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张墨告诉南风窗,学校对她的考核要求,是5年内要拿到一个厅级基金项目,在核心期刊上发表4篇学术论文。 合同写明,如果没有完成,她会被调离岗位。
这套以学术科研为重点的考核不仅关系到青年教师能否留聘、入编,也和他们的职称晋升、薪酬待遇、评奖评优捆绑在一起。
目标导向是明确的,也是单一的。势态也逐渐扭曲变形。
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统称为“教师”的群体并不全然授课。
操太圣告诉南风窗,前几年很多“985”高校招了大量年轻博士,进的是专职科研岗,他们的任务不是教学,不需要上课,主业就是做课题、做基金项目、写论文。如此设置的原因之一,是适应学校发展需要,体谅老师若同时兼顾教学和科研,分身乏术,两头不讨好。
很多高校招了大量博士,任务不是教学
相比之下,学校招聘的教学岗,名额有限。“但后来我们了解的是,教学岗竞争丝毫不比科研岗弱,只看教学又不行了,最后又变成了想方设法去弄一些跟科研相关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加分项。”
部分因为科研考核压力,张墨从浙江一所排名更靠前的大学转到了如今的学校,而她发现,两所学校都有“一些老师课时量不达标”的现象。
“那边有些老师不上课,是本来到手的工资就五六千的水平,也不在乎扣那点绩效的钱,自己在外面开公司做工程;现在这边的学校,一些老师会多抽时间在家里照顾小朋友,因为之前课时量达不达标,钱都照发。”但她说今年有了变化,学校增加教师课时量了,也规定不达标扣绩效工资。
2012年,持续关注青年群体、提出“蚁族”概念的学者廉思出了一本书《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在“非升即走”尚未普及之前,他就关注到了大学青年教师的困境。
“我一直认为《工蜂》深度比《蚁族》好,但是当年没什么反响。”廉思告诉南风窗,“倒是最近这几年,这本书被反复提及。”
廉思以“工蜂”类比如今的高校青年教师,工蜂的体型比蜂后及雄蜂都小,是蜂群之中的绝大多数,它们担负了整个蜂群的全部劳动,也筑起整个蜂巢,勤苦一生。
大学青年教师的处境与之类似。“科研经费、职称晋升、学术成果、教学评估、结婚生子、兼职收入,这些本身并没有关系的词语,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下发生了复杂的因果联系。”廉思在序言中写道, 而在以权力、财富为核心的世俗评价标准中,这些因素让这一群体在不上不下中更显尴尬。
在《工蜂》对高校青年教师、学者名家的访谈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指向“量化指标考评”。
操太圣对此也有体会,他告诉南风窗,高校会将学术期刊分等级,一类、二类、三类,要求老师在相应等级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评价的时候根据论文发表篇数和等级赋予不同的分值,科研也按是申请到了国家级或省部级的基金项目,赋予不同的分值,一本专著折算成2~3篇C刊论文,一些奖励、咨询报告最终也换算成分数进行评价,“一切东西最后都强调可见可比较”。
这种手段看起来客观公正且简单,但一如前文所述, 能产生量化指标的科研学术更容易被认为是有用的,而不能产生量化指标但有价值的事情,便少有人做了。
就连“可见可比”也只是相对的。“假如本来我们有2篇C刊、一个省级项目就可以评(副教授职称)了,但如果十几个老师都完成,门槛是不够的,最后有限的名额当然给成果越多的老师。”张墨说,教师也被推着用更短的时间出更多的成果。
“现在的问题就是每个老师都要去发,博士生也要去发,这么多的作者,但是又相对小的发表空间,压力特别大。”操太圣说。
研究者的应对之法中,发不了国内等级高的期刊,就往国外期刊上投,哪怕研究的其实是国内话题;又或者为了够到考核标准,尽可能在等级低、容易发的期刊上多发几篇,以量凑分。
强大的需求,也逐渐把论文发表变成一门围绕版面费、考验人脉的生意,也给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土壤。
相比论文,青年教师更愁的是基金项目申报。期刊审稿退稿周期短,还有其他期刊可另投,多少可控;国家级的科研基金项目每年就那么多,今年没拿到,只能等来年。在主管部门下发申报通知之前,许多学校提前数月就开始筹备,而春节打磨“本子”(即基金项目申请书),也成了青年教师的集体“年俗”。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青年教师连报三五年都没拿下。
相比论文,青年教师更愁的是基金项目申报 /《黑狗》剧照
数据直观显示出竞争的残酷。2023年,申请了当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超过30万个,获得资助的是4.87万个,而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数为4790项,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31~35岁的青年申请者最多,占比超三分之一,竞争尤为激烈。
《工蜂》当中,廉思回收了5138份的调查问卷,其中关注到一个现象:青年教师眼中,除去论文、基金项目本身的质量外,影响结果的重要因素,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分别为人际关系、职称、发表费用(单指论文)、学校名气、研究方向,没有人认为影响论文发表、项目申请的因素仅仅是质量。
2012年,在《工蜂》的访谈中,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直言,从争学校排名到争各种“青年计划”,“整个儿是一个指标系统,大到一个学校,小到一个老师,都是用一套指标系统衡量。人只是为了赚工分,创造已经不重要了”。
工分争夺赛里,总会有人站上前排,只有少数的蜂后和雄蜂能够胜出,却以巨大的成本牵动着整个族群里的工蜂。
从“985”高校文学院“非升即走”后,余薇去了留学过的日本找到了新的大学教职。
面试过程中,她翻译的一位日本当代女性作家的小说集,得到了面试官的认可,对方饶有兴趣地问她,能翻译这位作家的书是有什么门路,她备受鼓舞。
余薇从中发现了两套不同的评价标准:“在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哪怕你是做翻译研究的,哪怕你是文学院的,文艺作品的翻译都不被认可。曾经有人劝我别翻译小说,浪费时间,我觉得他说得对,可我没听,因为我是女作家粉丝。”她记叙道。
对比之下,在紧张的考核时间内,沿着“唯论文”“唯项目”“唯职称”的指标考核走,也的确助长了短期功利行为。
操太圣告诉南风窗,逼出来的一条捷径是追逐热点。去看政策热点是什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写了什么,把着期刊发表门关的编辑更容易看中哪些话题。
无形当中,老师和研究者也在让渡研究选题的自主权,然而“被选中”的同时,额外的代价却被忽略了。 政策热点常常变化,切换当中,损伤的是学术研究中至关重要的系统性。
基金项目也有“重申请轻研究”的现象。这说的是,花大力气拿到了国家级基金项目或子课题,但没有在期限内完成,最后结不了项,相应的科研经费被收回,研究者被除名。但在此之前,一种怪异的行为已经出现:拿到了国家课题几乎变成一种荣誉,大家可以用它申请其他奖项、人才帽子、更大的项目,这个课题就不管了。
“如果真正是要重视科研,评价就不要只是看你有没有拿到什么级别的项目,而主要是看你怎么研究,最后做没做出来真正有学术水平的成果。指挥棒如果指不准的话,大家就会关注那些形式上的东西,作为目标本身去追求,而偏离了本质,带来很多危害。”操太圣说。
基金项目也有“重申请轻研究”的现象
以“唯论文”为起点,“唯项目”“唯职称”“唯奖项”“唯帽子”(注:各种享有特殊待遇的人才称号,如长江学者、泰山学者)其实相辅相成、彼此强化,沿着单一的路径,资源愈发向少数人集中,也强化了单一的成功观,由此和多元的学科特点发生冲撞。
操太圣告诉南风窗,注重论文、重视引用率、量化实证最早更多是理科的判断标准,但很快影响到其他学科。早有工科教师提出批评,工科侧重工程和应用,天天发论文那怎么行呢?时至今日,“工科理科化”的批评声仍在。
操太圣所在的人文社科同样难受,“人文社会学科看重专著,以前老先生更是如此,需要足够的篇幅不断论证辨析,一写就是十几年,思想性才能形成。现在我们以论文评价为主,篇幅已经限制了论证,也没有长时间的沉浸式思考,还说专著折算成两篇c刊。”
《工蜂》当中,记录了一位青年教师的憋闷。
他常常要和自己不感兴趣的课题打交道,这让他倍感如芒在背。
喜欢的课题,再枯燥、再漫长他都愿意做,还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任务;而对不喜欢的课题,他有五花八门的比喻,“简直就像上刑场”“就像说服自己接受一个不喜欢的异性”,心里非常抗拒,即使是举手之劳也不愿为之。
有人劝他,做课题早晚是那么一哆嗦,你还在那里磨蹭个啥?他回,你不知道,难就难在接受“那么一哆嗦”。当学者就像开汽车,人毕竟是有性情、有偏好的,有时候就只愿意朝这个方向开,难就难在让他转向。
访谈者记录下他的许多语录,其中一句是:“天天逼着教师开窍,却搞得他们很不开心。既然不开心,开窍也就免谈了。 管理者只知道开窍之重要,却从不关心教授是否开心。”
开心,那不只是名和利的问题。
“我们高校教师本质上是这样一个群体,自主、追求精益求精和不断超越。只谈要求,不顾他人的选择,蔑视人家的自主性就是麻烦的事。”操太圣说。
关注它,能让你听到更多真话,
一 周 热 点 回 顾
2024 Vista看天下
Manner 咖 啡 的 性 价 比,全 靠 欺 负 员 工?
这 网 红 小 吃 凉 了,店 主 赔 哭 了
遍 地 长 毛,“南 方 人 已发 霉 求 放 过”
职业成为围城↓↓↓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工作压力大,没法排遣。 人人都虎着脸对着你,你想求人帮忙都没办法。 有时候会想到自杀算了。 哎。 这日子有的熬啊。
教师工资既然这么低,老师为什么不辞职
如果老师们都辞职了,谁来教育孩子?那些选择教师职业的可都是正规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当初选择做老师,是因为教师是个受尊重的职业,而且工资福利也不错。 之所以现在男生不选择教师这个职业,主要原因就是老师的工资太低。 所以,解决问题的根本不是让老师辞职,而是国家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师地位,让教师真正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
中国数学家的小故事
1962年12月22日印度发行弓一张纪念邮票。 这张邮票是为纪念印度的「国宝」锡里尼哇沙‧拉玛奴江(Srinivasa Ramanujan)诞生七十五周年而发行的。 拉玛奴江是一个生於南印度没落的贫穷婆罗门家庭,没有受过大学育,靠自学及艰苦钻研数学,后来成为一个闻名国际的数学家。 在数学家中,以贫穷家庭出身,而且能在没有研究数学的环境裏,孤独的工作,发现了一些深入的结果的人是不太多。 他到了二十七岁时才获得真正数学家的教导,他的才华像彗星突然出现长空,耀眼令人侧目。 可惜的是肺病却蚕食了他的生命,他在三十三岁时悄然逝去。 他是淡米尔人,生於1887年12月22日,父亲是一间布店裏的小职员。 小时候他大部份的时间是在祖母家裏度过。 从小他就喜欢思考问题,曾问老师在天空闪耀的星座的距离,以及地球赤道的长度。 在十二岁时始对数学发生兴趣,曾问高班同学:「什麼是数学的最高真理?」当时同学告诉他「毕达高拉斯定理」(即中国人称「商高定理」)是可以作为代表,引起了他对几何的兴趣。 有一天一个老师讲:「三十个果子给三十个人平分,每一个人得到一个。 同样的十四个果子给十四个人平分,每一个人得一个果子。 」从这裏老师下了结论:任何数给自己除得到是一。 拉玛奴江觉得不对,马上站起来问:「是否每一个人也得到一个?」这时数字的奇妙性质引起了他的注意,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他对等差,等比级数的性质自己作了研究。 在十三岁时,高班的同学借给他一本Loney 的〈三角学〉一书(以,前,有一些学校采用此书为高中课,中译本书名为〈龙氏三角学〉),他很快把整夬书的习题解完。 第二年他得到了正弦和余弦函数的无穷级数展开式,后来他才知这是著名的Euler 公式,他心中有点失望,於是把自己结果的草稿,偷偷地放到裏的屋梁上。 他十五岁时,朋友借给了他二厚册英国人卡尔(Carr)写「纯数的应用数学基本结果大要」一书。 这书是写得相当枯燥无味的,罗列了在代数、微积分、三角学和解析几何的六千个定理和公式。 这本书对他来说是本好书,他自己证明了其中的一些定理,而以后他研究的基础全是这书给出的。 在1930年他进入了家乡的政府学院,由於贫穷和入学试成绩优越,他获得奖学金,可是在学院裏他太专心於自己善羑的数学,而忽略了其他科目,结果年考不及格而失去了奖学金。 在1906年他转到另外一间学院读二年级并参加1907年的「文科第一考试」,。 是又失败了。 在1907年到1910年之间,他住在外面,找不到任何工作,有时替朋友补习以换取一些吃的东西。 在这段期间,他自己研究魔方阵、连环分数、超几何级数、椭圆积分及一些数论问题,他把自己得到的结果写在二本记事簿裏,生活不安定不能使到他对数学的爱好减少,一个善良的邻居老太太,看他生活困难,几次在中餐时邀他在家裏吃些东西。 根据印度的习俗,他家人在1909年为他安排了婚事,妻子是一个九岁的女孩。 在1910年他是二十三岁了,有了家而且因是长子,必须帮助家一些费用,他不得不极力寻找工作,后来朋友推荐他去找印度官员拉奥。 拉奥本身是一个有钱的印度官员,也是印度数学会的创办人之一,认为拉玛奴江不适合做其他工作,很难介绍工作给柋,因此宁愿每个月给他一些钱,够他生活不必去工作,而他自己可以作研究。 他很赏识拉玛奴江的数学才能。 接玛奴江只好接受这些钱,又继续他的究工作。 每天傍晚时分才在马德拉斯(Madras)的海边散步和朋友聊天作为休息。 有一天一个老朋友遇到他,就对他说:「人们称赞你有数学的天才!」拉玛奴江听了笑道:「天才?!请你看看我的肘吧!」他的肘的皮肤显得又黑又厚。 他解释他日夜在石板上计算,用破布来擦掉石板上的字太花时间了,他每几分钟就用肘直接擦石板的字。 朋友问他既然要作这麼多计算为甚麼不用纸来写。 拉玛奴江说他连吃饭都成问题,那裏有钱去买大量的纸来用,原来接玛奴江觉得依靠别人生活心里是很惭愧,已经有一个月不去拿钱了。 很幸运拉玛奴江获得了奖学金,在1913年5月开始,他每个月获得七十五卢比。 不久他的朋友协助他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数学家哈地球()教授,在这信裏列下了他以前研究得到的一百二十个定理和公式。 哈地教授看到他的一些结果,有些是重新发现一百年前大数学家的结果,有一些是错误,有一些是非常深入困难,经过许多波折,拉玛奴江总算来到了英国。 哈地认为要教他现代数学,如果照常规从头学起,很可能会对拉玛奴江的才能有损害。 而他又不能停留在对现代数学无知的状态。 因此哈地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帮助他学习,终於拉玛奴江掌握了较健全的现代分析理论的知识。 比他教给拉玛奴江的还多。 从1914到1918年拉玛奴江和教授写了许多重要的数学论文。 由於他是个虔诚的婆罗门教徒,绝对奉行素食主义,在英国生活那段时间,他自己煮自己的食物,而常常因研究而忘记吃饭,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后来常感到身上有无名的疼痛。 后来才发现他患上了无法医治的肺病。 在英国医院住了一个时期。 哈地教授讲他在病中的一个故事:有一天哈地乘了一辆出租汽车去看他,这车牌号码是1729。 哈地对拉玛奴江讲出了这个数字,看来没有甚麼意义。 可是拉玛奴江想一下马上回答:「这是最小的整数能用二种方法来表示二个整数的立方的和。 」(1729=13+123=93+103)拉玛奴江被称为数学的预言家,他死后已经有五十四年了,可是他的一些预测的结果,还是目前数学家正想法证明的。 他在1920年4月26日死於麻特拉斯,马德拉斯大学后来建立了一个高等数学研究所,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而在1974年还准备在研究所门前为他矗立一个大理半身像。 如果他英灵有知,或许他会说:「不必替我立像,应该求求那些正在饿死的小孩,他们有许多会是未来的拉玛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