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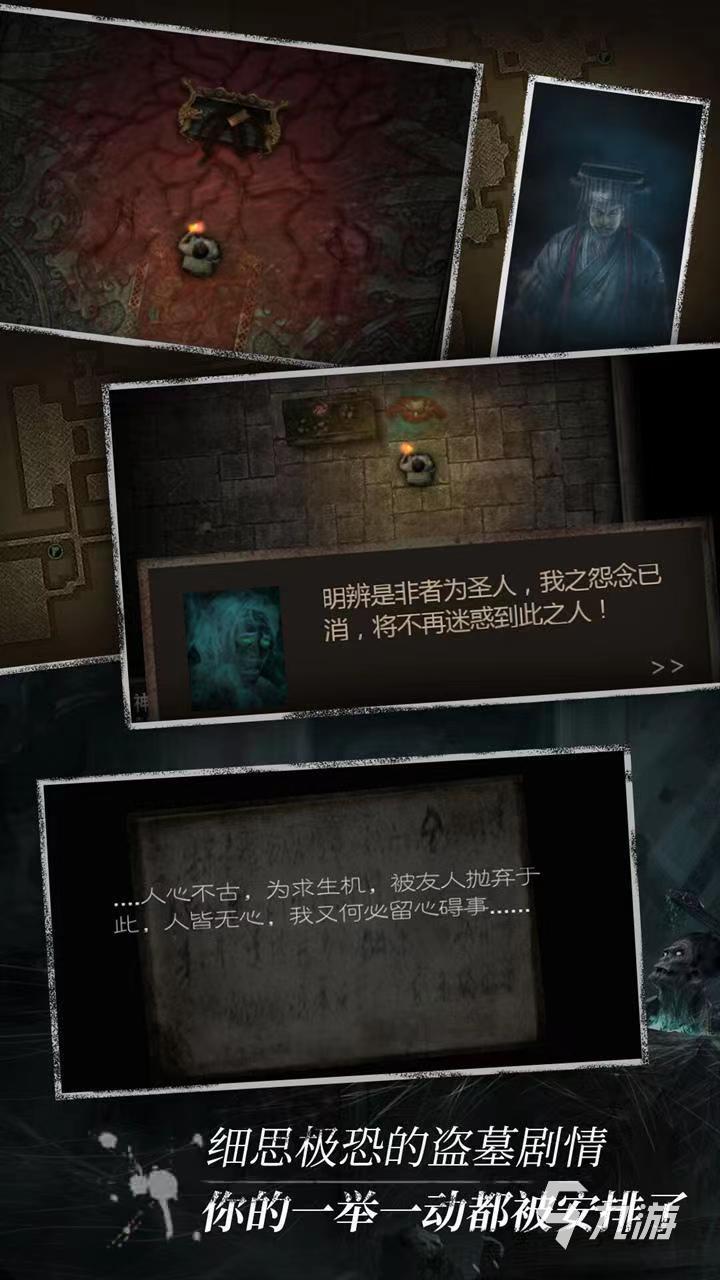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人类学系博士葛韵
从海昏侯墓到三星堆,从商代鸮卣到河光刻石,考古意外地成了21世纪最能破壁出圈的学术领域。公众与历史的距离从来没有如此贴近过,很多年轻人爱上了田野考古和博物馆,考古学也不再是冷僻、乏人问津的专业。
考古到底是什么?考古学家寻找的是什么?考古学的真正社会价值在哪里?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考古学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在《考古学是什么》一书中,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向公众普及了考古学这门学科。
近期,陈胜前教授与考古学博士葛韵进行对谈,他们从各自的视角,畅谈自身经历过的田野挖掘、奇趣发现和考古研究,告诉读者“考古是什么”。
考古就是“器以载道”
主持人:虽然考古在当下是一个很火的话题,但还有很多人理解的“考古”可能并不是专业考古学者所熟悉和接触的“考古学”。那么,你们从事的“考古学”,到底是什么?
陈胜前:什么是考古学?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通过去找到物质遗存,去分析物质遗存,去解读物质遗存,来探索人类过去。从这一角度讲,它跟自然科学是很像的,面对的都是客观实在的东西。人类的过去是客观的,不论我们能不能认识它,它都在那里。不过,很多人认为,既然考古学是一门科学,就应该像自然科学一样。但是考古学好像又不完全是一门像自然科学的学科。考古学只要涉及到人,就必定涉及到人的社会。人是社会性的,是历史的存在。因此,考古学研究不可能完全像研究自然科学一样。比如考古学关心等级的起源、战争的起源、国家的起源、民族的起源,都是跟考古密切相关的。所以说,考古学也是典型的社会科学。
考古学还是人文学科。人文是赋予意义的学科,虽然考古学对于物质遗存的认识在一方面是客观的,但是人赋予了物以意义。比如,竹子本是禾本科的植物,跟气节之间没有固有的逻辑关系,是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赋予它的意义,这不是自然科学的东西。意义对群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到它的价值认同和群体存在的意义。很多时候,有人认为历史学、考古学是求真求实。这句话说对了一半,另外一半是涉及到意义的。我们怎么来评价意义呢?意义涉及到善恶、美丑,它不是真伪的问题。考古学研究的物质是承载着意义的,历史不仅仅在文字里面,它还有很大一部分在实物里面,实物是极好的文化载体。我们一般说“文以载道”,而考古是“器以载道”。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古又是一个人文学科,它具有特别重要的精神意义上的价值。
葛韵:考古学就是通过研究古代人类留下的物质文化遗存来重建古代社会的一门学科。从定义来看,我们首先要获得这些物质文化遗存,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在构建古代社会的时候,我们没法回到过去,我们所说的意义也跟时代背景和个人的经历有关,因此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角度去构建古代的社会。
当我们谈及考古学的时候,很多人会把考古学跟历史学相联系。但实际上,考古学跟历史学最大的区别在于“物质性”。因为文字可以作伪,比如我在写一句话时可能说“我现在非常不紧张”,但实际上我非常紧张。但是我留下的物质遗存就证明了我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考古相比于历史学而言,会更加客观。因为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在欧美地区,尤其是在北美洲地区,考古学是分属于人类学的,有更加全面的界定。人类学分为四个方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这些学科通过不同的角度、方法,来构建出从古至今,乃至未来人类社会的走向问题。我觉得考古学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像我们看到的当今的社会问题,甚至气候变化问题,都是考古学研究中很重要的问题。考古学研究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经验,去指导我们以后走向哪里。
考古非常像刑侦破案
主持人:很多人提到考古,自然而然会联想到的词是盗墓。在很多流行文化上,像《盗墓笔记》,向大众灌输一种好像考古学和盗墓是紧密相连的概念。那么,我们怎么看待流行文化中传达的与考古看似有关联的形象塑造?它和真实的考古学,有什么样的差距?
陈胜前:从科学角度来看,考古非常像刑侦破案。我们跟刑侦学家有很相似的地方。我们到了现场,首先都是保护现场,挖到东西之后,千万别动它,它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动了它的位置就会影响信息的解读。好比说这个地方经过水流的冲刷,它的高低、倾角,对我们判断水流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发掘两三万年前的火塘的时候就注意到西北面的东西很多,为什么其他三面东西很少呢?因为当人们坐在火塘边,有烟熏的那一面不坐人,就都往那边扔废品。从这个现象,一下就看出来现场是刮的东南风,这个地方属于季风区。这个遗址位于长城脚下、沙漠边缘,冬天根本没法待。火塘边发现的石片都很小,说明人在那里是修理工具,他就把那些东西扔到边上,动物骨骼都很细碎。古人不可能一清早就去打猎,往往在火塘边吃的是带回来的前一天剩的东西。
第二步也跟刑侦一样,就是我们把标本送实验室。年代学的标本送年代学的实验室,动物的标本送动物实验室,植物的标本送植物考古实验室,还有DNA标本、同位素标本等。我们现在基于同位素可以知道他的家乡是哪里,他小时候是在哪里生活的,吃的肉多还是少,吃的是不是农作物等,这些都可以根据同位素检测出来。
不过,第三步有点不太一样,刑侦学家比我们有优势。例如出现凶杀案现场,刑侦学家不会认为所有人都有嫌疑,他们是有模型的。劫财、复仇、斗殴等案件,都有相应的模式,他们根据模型去找线索。如果刑侦学家没有模型,那么破案的难度就非常高。
对考古学家来说,我们现在特别缺的就是模型。尤其在史前时代,如果没有模型,又对这种生活不熟悉,当我们面对这个场景时,要解读就变得特别困难。当我们有了模型,再去解读这些材料,更可能知道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考古学在史前考古领域比较薄弱的就是理论的构建部分,也就是模型的构建,这造成我们在考古推理过程中遇到问题。

最近安阳殷墟新开的博物馆里有个展厅非常好,单独讲一个叫“亚长”的人的故事。他的墓和他几个随从的墓正好都没被盗,信息完整丰富。墓位于殷墟,但同位素分析显示他们是河南东部的人,可能是从商的附属国来的,帮忙打仗。他死的时候大概35岁左右,身上有七八处伤,有一处伤是比较重的。这些都给保存下来,被考古学家发现了,经过分析之后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出来。
盗墓只是个人能得到一点点好处,而对我们了解人类过去来说是灾难性的。盗墓让古物脱离了它的原境,损失了众多关键信息。考古里面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年代。如果没有确切的年代,后面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亚长墓如果被盗的话,我们见到那里出来的青铜器,就不知道它的年代,只能猜测是商代的。但是很多器物会传世使用,商代的器物可能在战国时期埋到土里,早期的东西埋到晚期的墓里,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它被破坏了,我们根本研究不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所以,盗墓跟考古,先天就是敌人。有盗墓者,考古就搞不了。盗墓者只为了个人的一点点贪念,却破坏了后代的文化研究,这是非常可鄙的一件事情。
考古工作者,是古代人的人生见证者
主持人:在我们获得考古材料之后,仍然需要很多对它的再处理、解释。把它们翻译成我们理解的因果关系。在此以外,考古学不是只有理论上的讨论,它还必须要面对实际的田野活动。那么,两位老师在自己的田野考察经历当中,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和经历的体验呢?
陈胜前:从事一项职业之后,慢慢地就没有神秘感了,就像作为医生看到人体一样,就都是器官组织。我想过这个问题,可能是我刚进入到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的本科在吉林大学学的考古,大三的时候去赤峰发掘白音长汗遗址。从赤峰市到遗址,三百多公里路,要坐一天车。一下车,天开地阔,特别震撼。我是湖北人,在南方看到的天经常是低矮的,内蒙古不一样。我们发掘的遗址是八千年前的两个村落,村落中间有浅浅的壕沟分开。这个遗址有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五种遗存。其中以兴隆洼文化为主,不只有八千年前的房址,也有六七千年前的房址。
我在那里挖的最好的房子是八千多年前的,房子一般有40平方米左右,可以看出兴隆洼文化的人群日子过得很精致。房址中间是用石板砌成四方形的火塘,火塘前面还有袋状的储物坑。开口比这小圆桌面还小一点,人在里面活动不开,只能头转进去挖。判断灰坑需要看土质土色,因为只要是人类动过的土,它的颜色跟自然生土是不一样的。在北方生土是黄色的,但人动过了之后,就会混入杂质,有的发黑,有的带一点黄褐色,也就是所谓的花土。房址中的居住面是用细泥抹过的,跟生土完全不一样,看见了,肯定就知道挖到居住面了,不可能挖错。另外,挖到石板灶也就知道挖到居住面了,就像是居住面上铺了地毯似的,不可能弄错的。房址中间区域抹细泥,边上起土楞,土楞外边是生土,明显不一样。有的房址里面陶器倒扣着摆放,数量还很多,好像人才刚刚走似的,保存得非常好。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可能是因为早期农业群体定居能力还不强,人们还需要在几个居址之间迁移。要去一个地方,过一段时间再回来,离开之前,都会把家里东西收拾一下。比如说,我要是离开半年,我可能只会把暂时需要的东西搬走;如果是彻底放弃,那么家里什么都不会留,到了最后阶段可能会进行破坏,不要的东西,砸了也不可惜。我们看到的比较晚的史前遗址,发现的往往是一些破烂,器物都不完整。相反,八千多年前的遗址保存几乎都特别好,所以我们都特别喜欢挖这个时期的遗址,房子里面东西特别多。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考古所见的共存不等于相关。我们发现这些东西在一起,不等于它们是必然相关的。比如我在一个洞里挖到许多动物化石,也发现了人类化石,它们是在一起出土的,这证明它们的年代相同,但不能证明它们必然有相关性,不能说这些动物就是人类狩猎的。哪怕是考古工作者,实在是想得到一个解释,往往也会把共存性当成了相关性,认为这些动物就是人们狩猎得到的。
葛韵:陈老师主要讲了一些思辨性的事情,在遗址里发现什么东西,去考察它到底形成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等这些问题。那么,我来谈一谈考古里会让人感觉不一样的东西。现在流行一句话叫做“人生是旷野”,考古其实是旷野之外的旷野。
很多人可能会想象,考古可能是进入深山无人的荒区里进行发掘,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但是我比较幸运,我本科发掘是在河南的濮阳西城遗址,那是一个非常好的遗址公园。我本来雄心壮志,觉得在那里肯定能找到很多改变中国历史的东西,结果向下发掘了三米,只找到一些汉代的陶片,再无其他。后来硕士期间去了二里头遗址,这是中国非常重要的青铜时代遗址,我觉得这回可以大有作为了。结果被安排的工作目标是找五号宫殿基址的南墙,也确实找到了。当然,在这些过程中,也是有很多思辨性的问题。
再到后来,我跑到了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遗址做考古发掘,我时常会想,考古的魅力在哪儿?它不光是这种思辨性的收获,能够去琢磨古代的社会是什么样,而且考古让我更多地接触到了不同的人,他们的人生非常简单,以至于当我在和他们交流时,我甚至感觉自己是他们人生的一个见证者。
此外,当我发掘了一天累到不行的时候,我们收工一般都是太阳下山的时候,当我在遗址前面,去感受时间的变化,以及太阳落山那一刻,阳光打在我的脸上有温暖的时候,简直太幸福了。那种慢节奏的生活在城市里边基本上是感受不到的,我觉得这就是田野时期的魅力所在。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不只是农民,还有我们考古工作者。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苦中作乐,我不管穿什么样衣服,到了工地一天下来浑身都是土,脸上都是土。我即使戴着口罩,鼻孔这两个位置全是两个黑土,全都被土给掩盖了,但我依然感到非常的美好。
“陶寺”“新砦”“二里头”,绝对达到了国家的社会复杂程度


读者:老师们好。虽然我是外行人,但是想问一下现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还在进行吗?学界对工程的反响如何?
陈胜前: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准确地说“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结束了。它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进行的,持续的时间不长,大概有六年左右。从2000年至今,开始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有一个项目叫“考古中国”。
关于夏代的考古,如今非常热,考古界和史学的一些老师们认为“夏代无法证实”“夏代是传说”。我不是特别赞同这样的观点,从考古学上讲,夏从公元前2100年左右到17世纪这么一段时间,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像陶寺遗址、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绝对达到了国家的社会复杂程度,剩下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确认它。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是我们的臆想,不是自我的吹嘘。因为五千年前良渚古城算上外廓城将近600万平方米了,还有专业化的玉器工业和复杂的水坝系统。现在不只有一个遗址,还有更早的凌家滩遗址,一个墓里面就出300多件玉石器,还有3000平方米红烧土,可能是宫殿遗迹。最近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挖的南佐遗址,也接近5000年前,有800多平方米的大殿,一个柱子的柱础直径就有近一米,另外还有9个夯土高台,每个高台都十几万立方米的土方量,基本上都达到了国家的复杂程度。
某种意义上说,有关夏的问题其实不是科学问题,而是话语权的竞争问题。哪种历史可以证实?科学只能证伪,我们能证实吗?比如有人说证明夏一定需要有文字,即便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夏”字,我说这个不一定是指夏朝,可能说的是指季节,如何证实呢?我们无法回到过去,要证实太难了。但是时间对得上,地方对得上,社会发展水平对得上,也有文献记载,为什么不能认为是夏呢!
葛韵:我觉得考古学的魅力在于它是可以多元阐释的研究,也就是说面对同样一批材料,我们不一定非要得出单一的结论。有关夏或者非夏研究,我个人没有太多观点。但是我需要补充的是,考古学它可以促进所谓的社会公益或者社会正义。在中原中心形成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中原的这几个文明,还有其他周边的文化,我们也需要关注。所以,当我们谈及考古学为中华文明的认同、贡献有什么作用时,不能仅限于夏商周中心的这些文明,像三星堆,西北地区的一些同时期的文化也很重要。






